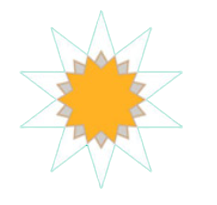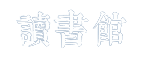從山鄉看社會變遷
中國社會百年大變,處處,人人都留下變遷的印記。近年與故鄉接觸較多,心弦一再被觸動,這不就是中國變遷的側影嗎。發願記下,又深感動手晚了,先輩一一離去,許多情況難於弄清了。亡羊補牢,隨手記下若幹鱗爪,為家鄉的過去留下幾片枝葉。疏漏之處,留待異日修改補充。
離鄉別井65年了。家鄉不但給了我永世不變的鄉音,也留下一些無法磨滅的記憶。
我1931年末來到世間。按照當時的稱謂,出生地是廣東省興梅專區興寧縣羅崗區。那時,汕頭和周邊各縣大部分被日軍占領,興寧成了粵東的政治經濟中心。興梅專員公署設在這裏,管轄興寧,梅縣,平遠,蕉嶺,五華等縣。經濟畸形繁榮,與韶關和江西來往頻繁,紙醉金迷,商業很發達。紡織和釀酒,造紙,制筆墨等手工業也頗為興盛。它又是軍事中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閩粵贛邊區司令部就設在興寧縣城郊神光山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治掛帥,興寧和梅縣的地位倒過來了。葉帥的故鄉是梅縣,梅縣就跑到前面去了。即使在梅縣,原來公認梅州中學比東山中學辦得好,但東中是葉帥的母校,各方大力扶持,自然把梅中拋在後面。地區招牌變換幾次,現在叫梅州市,興寧歸其管轄。興寧長期叫縣,幾年前也改稱市。羅崗則過去叫區,現在叫鎮。政治變幻改不了百姓的習慣,依然稱為興寧羅崗。
羅崗是興寧北部的山區,隔幾十裏地,就是江西南邊的尋烏。
以我家所在的蕉坑村來說,它在區政府所在地羅崗圩旁邊,但開門見山,舉目是山。山,永遠是那麼翠綠。筆直高大的杉樹,無邊無際的松濤,漫山遍野的魯箕,還有一片一片的油茶,柚子和杜鵑。坐在家裏就能聽到雉雞飛鳴。要是正在念高中的蕉村叔在家,往往立即拿起獵槍趕去,我則跟在後面去撿獵物。從大人口中常常聽見哪裏有老虎,豹子露面。後生們不時上山打野豬,黃猄,常常可以吃到他們的戰利品。有一年我還看過一幫人在羅崗圩尾河旁劏老虎,腥味四溢,而人們久久不願離去,圍觀這難得一見的盛事。家鄉人相信戴上頸圈,鬼神攝不走孩子的靈魂。我小時候有一個銀頸圈,上面掛著各有寓意的小物件,其中就有一顆虎牙。
這些動物經常出沒的地方意味著什麼。山林茂密!蕉坑村有一個地方叫崩崗灣裏,顯然是山體滑坡的遺痕,我記事時,那裏已長滿密密麻麻高大的松樹,杉樹,遍地魯箕。各間圍龍屋或四角樓後面肯定有一片或大或小的風水林。動風水樹,神人共憤,沒有人敢輕易嘗試。當時沒有聽說過環境保護四個字,實際上人人註意保護環境,難怪家鄉如此優美。
最迷人的是水!彎彎曲曲的羅崗河,十多二十米的河面,兩岸是連綿的翠竹,蘆葦和赤孽花。水車,水碓,陂頭點綴其間。蕉坑村前面的羅崗河有兩條水陂(水壩),最大的是柳樹陂。水陂是用松樹為骨幹,再用魯箕草和砂石塞住空隙。松樹不怕水,越浸越硬,這樣的水壩容易修築,卻不易沖垮。陂頭上彎彎曲曲的河道既寬又深,實際是頗具規模的水庫。附近的農田因此可以自流灌溉,收成很穩定。只有大旱年景,才用得著腳踏或手搖的水車。陂頭的小瀑布下是小水潭,夏天放學後,孩子們都到那邊去玩水,一片歡聲笑語。
白天,不時有木排,竹排越過陂頭,順流直下,可以到達興寧縣城。羅崗圩屹立在河邊,一邊是街道,另一邊是豎滿杉樹,綠竹的約十間做竹木生意的樹園。每間周邊是木片釘出來的樊籬,與河邊的柳樹相映成趣。
粗壯的麻石嵌出來的壩尾橋,有個突出的橋墩,我喜愛坐在那裏發呆,仰望藍天遠山,俯觀清流激浪。去白水寨外婆家,或者學校帶我們到到雷公岬遠足,都可以看到飛流直下的瀑布。此外,去深不見底的柳樹陂釣魚,運氣好可以釣到一斤左右的大魚。有時背著小魚簍跟著蕉村叔去河裏打漁,背回來一兩斤魚並非難事。
家鄉是廣東省認定的著名古村落之一。先祖父述初公營建善述圍是這條古村落的核心建築。人們談起客家人的建築,以為代表作就是圍龍屋,其實有另一類型叫四角樓,善述圍則是其代表作。灰塑,壁畫,刻在石柱上的對聯,印象中不比山西閻錫山的故居差。在中門的石柱上刻著兩句古詩,青山不墨千秋畫,綠水無弦萬古琴,正是羅崗美景貼切的寫照!
農村居民喝的是井水,但圩上居民就在河裏挑水喝。倒進缸裏後,用尾端挖了一個洞,內藏明礬的竹筒攪幾下,讓泥沙沈澱。
羅崗的水,也有為禍的時候。1945年夏天吧,大雨加上上遊的洪水沖來,大片農田被淹,水浸羅崗圩,好些店鋪倒塌,黎漢雄開的羅崗大飯店就倒塌了。最慘的是河邊的樹園,竹木漂走,房屋夷平。壩尾橋旁第一家樹園老闆張官麟被水沖走,屍體被沖到下遊十幾裏處。凹下的公路橋被沖毀,多年無法修復。
1991年,闊別44年後第一次回鄉,蕉坑村一帶的羅崗河成了小溪,羅崗圩旁邊的河面漂浮著各色垃圾,幾乎成為臭水溝!長排崗上的杉樹只有碗口大小。處處都記下歷史的深沈和艱辛。
什麼時候柳樹陂消失,羅崗河成了小溪。集體化後幾經折騰,各地林木遭殃,水流慢慢減少,木排,竹排消失。20世紀70年代農業學大寨,官員提出要去彎取直,增加耕地,改善灌溉。用心良好,辛勞苦幹,增加了十多畝耕地,改變了原有生態,羅崗河成了一條小溪,估計幾十年內都無法恢復原來的寬廣,幽美的狀態了。不能怪那些組織“會戰”的農村幹部,在計劃經濟籠罩下,他們肩負保障農民生活的重任,當時高官尚且不知環境保護為何物,何況日夜奮戰在基層的幹部!他們真心相信集體化——公社化——學大寨是康莊大道,有誰知道後果如此嚴重!
至於長排崗上的樹木,二十多年來,我多次回鄉看到,總是那麼稀疏,好像永遠長不大。我好奇地詢問,承親友們告知,盡管山地的產權劃分到戶了,但每戶只有一畝左右,那棵樹長到差不多了,老是被人偷去,大家就懶得經營了。記得文革期間在幹校,奉命幫助周邊生產隊,也累見好端端的樹,沒幾天準被人斬掉,只剩下樹根。集體財產,不要白不要,不是你偷就是我斬!沒想到幾十年後,流風余韻依然難於消除。
文/袁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