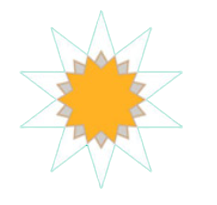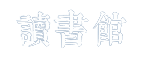緬甸醫生教導我~鴉片是吃的,不是抽的
最近我剛從東南亞考察了一圈回來。現在的東南亞的很多地方,特別是邊境地區,與上世紀末已經有了很大不同。秩序不像從前那麼亂了,同時也就意味著,奇奇怪怪有趣的事情越來越少了,越來越走向常規,與所謂正常社會的差別越來越小了,越來越少了雷效果的刺激。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常去東南亞做調研。有一次接受委託去考察中囯與東南亞之間的跨囯交通系統涉及的區域政治秩序是否穩定,大的交通項目若是鋪開建設是否可行。需要從雲南出境,經緬甸走兩三個囯家一直往南到出海口。事出緊急,來不及提前十多天打防疫針。即使立刻打針,也要一個星期後才能過境,等不了那個時間了。當時是4月,快要進入雨季,東南亞的一些傳染病對沒有抗體的外地人可能造成嚴重甚至致命的傷害。對此我絲毫不敢大意,因為就在一年前我出過一次事。
當時柬埔寨內戰結束不久,我去到很偏僻的一個鄉,到處有紅色高棉時期的萬人坑。天氣非常炎熱,白天我搭當地人開的摩托到處跑,晚上住在一個小客棧裏。兩三天以後,右腿的小腿肚開始紅腫,發展到後來慢慢化膿,但並沒有劇痛的感覺。我想可能是被蟲子咬了,問題應該不大,就自己用手把膿液擠出來,去街上找回來一瓶紅藥水塗上。十多天之後我回到香港,腿上腫的顏色已經不對勁了,中心的地方開始發紫,我趕緊去醫院找醫生。醫生對我說,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全香港開始放假,他的助手已經離開,他也買好了當晚的機票離港。但他必須要給我動手術,因為我不是一般的狀況,已經快接近敗血癥了,如果再耽擱幾天可能連那條腿都保不住不得不鋸掉!最後是他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用帶子把我綁在手術臺上,用刀把受感染最嚴重的組織挖出來,就像華佗給關公刮骨療傷一樣。那種錐心的疼痛,無法形容。我只記得當時兩只手死死攥住手術臺兩邊的欄桿,全身大汗淋漓,幾乎就要昏死過去,現在腿上還有兩個大疤。
事已至此,怎麼辦。到了雲南瑞麗一個囯境線上的村子,當地人告訴我,在村子屬於緬甸的另一邊有辦法。下午4點多,邊防員警開車帶我過境,交給緬甸一邊的村民,輾轉經過好幾個人的鏈條,我被帶進一個小院子。裏面有三四個小房間,客人在其中進食,互相並見面。食物是一鍋雞,很深的砂鍋埋在地下的土坑裏用炭火燜,鴉片是吃的,不是抽的。
鍋蓋四周封著土。我去後他們把砂鍋從地下取出來,把土刮掉,揭開鍋蓋,那個香味喲,一輩子從來沒有聞到過,它有一種滲透力,一直往你身體裏鉆。這雞有什麼講究。首先得是至少一年以上的老母雞,提前一天不讓它吃任何東西,只餵清水,目的是把腸子洗凈。大半天之後,把大煙土塞進它的嘴裏,有點像填鴨一樣,再餵它喝水。
到第二天中午,差不多24小時過去了,殺了那只雞,一點血不能流出,盡可能保持完整。接著放進砂鍋裏,燜上6個小時,才放在了我面前。他們說,要把腸子和內臟盡可能全部吃下去,湯盡可能全部喝掉,大煙土的藥性都在裏面。於是就著一碗當地的包穀燒酒,我從6點吃到9點多,基本完成了任務。也吃了一點雞肉,剩下的留給了當地人。臨走的時候,帶我去的人向我交代在接下來的時間裏可能出現的癥狀,說明藥在發揮作用。當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果然效果開始出現了。
第一個反應,五臟六腑裏熱火熏熏,再者,想喝水就喝水,想吃水果就吃水果,想喝白酒就喝白酒,除了西藥沒有禁忌,但是一天一夜之內都不感覺要上廁所。第二天下午我過境姐告,順著當地的土路一直往下走,大部分時間都在農村,條件差得一塌糊塗。當地人吃喝什麼我就吃喝什麼,他們生吃我也生吃,整整八九天,沒有任何蚊蟲叮咬我,也從來不鬧肚子,晚上睡覺好的不得了,一路暢行無阻。這在哪怕衛生狀況有了很大改觀的今天也是不可想像的,我習慣隨身帶很多止瀉消炎的腸胃藥,常常都還抵擋不住。就這麼一鍋雞的效力,能持續半個月不散。
很久以前我看過一本法文翻譯過來的書,叫做鴉片史,講述了為什麼鴉片在人類歷史上那麼珍貴。尤其在沒有現代醫藥工程的過去,許多的病痛無法醫治,但是鴉片可以。後來我常常感慨,如果能有辦法,使得大煙土像一般藥物一樣在藥房便能買到,同時又不至於被濫用,將減輕人類的多少痛苦啊。如果諸葛亮南征的時候瞭解了這麼一鍋雞的神奇,那麼蜀囯的命運恐怕也會改寫了。
這麼一鍋好雞,又有這麼多大煙土,多少錢,我付的是美元,折算成人民幣,也就差不多500多塊。這輩子吃過不知道多少好東西,惟獨這鍋雞,空前絕後。那種味道之鮮美不僅僅停留在舌頭上,連你的肌肉,經絡都能感受得到。所謂刻骨銘心,也就不過如此吧。